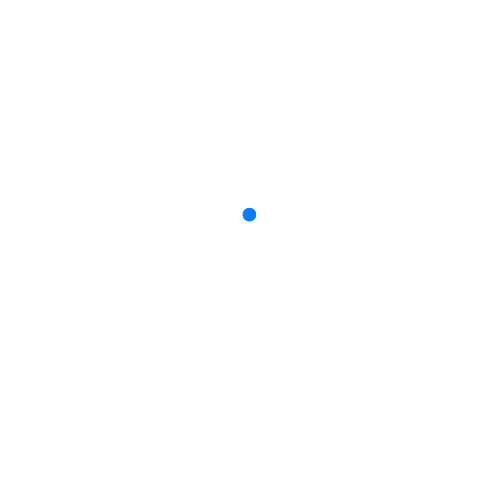协议约定竞业限制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剔除仲裁及诉讼审理期限错在哪里?
劳动合同到期终止时,公司没有要求秦仪婷(化名)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当她办完离职手续进入一家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工作20多天后,公司突然通知她履行竞业限制协议并接连给她发放2个月的经济补偿费用。秦仪婷不同意公司的要求,仲裁机构则裁决支持公司的请求。
一审法院审结本案时,秦仪婷已经离职12个月,该时间正好与她和公司约定的竞业限制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相吻合,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秦仪婷无需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但是,公司以双方曾经约定竞业限制期限应将仲裁和诉讼的审理期限扣除为由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虽然法律对于仲裁及诉讼程序的审理期限均有法定限制,但就具体案件而言该期限并非具体确定的期间,相当数量的案件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期间,因此若将其作为竞业限制期限约定内容不符合竞业限制条款应具体明确的立法要求。因公司的约定属于《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免除其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应属无效,故于3月11日终审判决驳回公司上诉。
是否履行竞业协议
离职之时未能确定
秦仪婷于2010年9月28日入职公司,双方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9年2月1日起至2022年2月28日止,其中约定秦仪婷担任高级总监。该劳动合同到期时,双方劳动关系终止。
此外,双方还于2019年2月1日签订一份《不竞争协议》,其中第3.1款约定:公司可以在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之日或之前,作出要求秦仪婷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选择,也可以作出放弃要求其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选择。若秦仪婷在离职之前或之后均没有收到公司关于是否要求其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决定,其有义务主动向公司询问该决定。
第3.3款约定:竞业限制补偿费=基数×1/2×竞业限制期限的月数。其中:基数=秦仪婷从公司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月工资;竞业限制期限从秦仪婷离职之日开始计算,最长不超过12个月,具体的月数根据公司向秦仪婷实际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费计算得出。但是,如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而提起仲裁或诉讼时,则上述竞业限制期限应将仲裁和诉讼的审理期限扣除;即秦仪婷应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期限,在扣除仲裁和诉讼审理的期限后,不应短于上述约定的竞业限制月数。
秦仪婷主张,根据第3.1款约定,公司至少应在她离职时告知她是否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而公司彼时并未对她进行告知,故她认为公司已经解除了《不竞争协议》,解除时间即为她离职时间,解除方式为公司未作出要求她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决定,且在离职清单中记载不向她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公司则认为,在为秦仪婷办理离职手续及2022年3月24日的通知中均明确要求秦仪婷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可见,公司已经作出了选择。
公司主张职工违约
要求继续履行协议
由于秦仪婷不同意公司的主张,公司以违约为由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庭审中,公司提交2017年3月9日为秦仪婷办理离职手续的清单,该清单载明:“1.支付《竞业禁止协议》补偿金:否;2.支付其他款项:否。”清单下方有如下打印内容:“本人确认如下内容:1.离职原因:个人原因辞职……3.如本人收到公司发出的《竞业限制补偿金通知》,则本人将严格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否则,本人认可并同意公司无需向本人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且本人无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该确认内容下方本人签字处有“张某(代)”字样。秦仪婷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称离职手续清单是劳动者办理工作交接的手续文件,不应附加放弃劳动者合法权利的格式条款,故该清单中所列格式条款无效。
另外,公司提交2017年3月24日通过EMS快递方式向秦仪婷发出《关于要求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和领取竞业限制经济补偿费的告知函》,载明:“公司告知并要求你遵守《不竞争协议》,全面并适当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秦仪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结合查明的案情,仲裁裁决秦仪婷双倍返还公司2022年3月、4月竞业限制补偿金共计177892元、秦仪婷继续履行对公司的竞业限制义务。

扣除仲裁诉讼审限
损害职工合法权利
秦仪婷不服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不竞争协议》第3.1款约定,秦仪婷离职时未收到通知并不必然免除其竞业限制义务。另外,离职手续清单载明,秦仪婷如收到公司发出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通知》,将严格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由此可见,彼时公司仍未免除秦仪婷的竞业限制义务。公司在秦仪婷离职尚不足一个月的时候向其发出告知函并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完全符合协议约定的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支付金额、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因此,秦仪婷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但在案事实表明其存在违约行为。
然而,一审法院认为,《不竞争协议》第3.3款约定竞业限制期限应将仲裁和诉讼的审理期限扣除是错误的。
首先,从立法目的出发,竞业限制制度的设置初衷不仅是要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不受侵犯,亦要保护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权和生存权不被过度限制,因此《劳动合同法》第24条第2款所规定的竞业限制期限采取了强制性规范的方式,性质上属于效力性规范,其针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以期将竞业限制期限规定在合理期限内。推及本案,公司在约定竞业限制期限时应当明确具体,以使劳动者对自身义务有合理预期和明确知晓,而不应当设置为不确定的期间段。
其次,从司法实践角度出发,劳动争议案件由于其特殊性,有相当数量案件需要经过“一裁两审”的程序,如将仲裁与诉讼的审理期间剔除在竞业限制期限之外,劳动者最终需要履行的竞业限制期限很有可能超过2年时间,与法律强制性规定相冲突,也可能导致用人单位为延长劳动者的竞业限制期限而滥用诉讼程序。
再次,从权利义务的平衡角度出发,用人单位作为格式条款的拟定一方,在缔约时比劳动者更具有优势,而公司关于竞业限制期限的约定势必给劳动者增加更多的义务,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用人单位的责任,导致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
综上,在秦仪婷的竞业限制期限已经届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秦仪婷向公司双倍返还2017年3月、4月竞业限制补偿金共计177892元、无需继续履行对公司的竞业限制义务。
针对公司的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从劳动者择业自由权角度来看,虽然法律对于仲裁及诉讼程序的审理期限均有法定限制,但就具体案件而言该期限并非具体确定的期间,将其作为竞业限制期限约定内容不符合竞业限制条款应具体明确的立法目的。加之劳动争议案件的特殊性,公司约定使得劳动者一旦与其发生争议,则其竞业限制期限将被延长至不可预期且相当长的一段期间。这就造成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权在一定期间内处于待定状态。
从司法救济权角度来看,如果仲裁及诉讼审理期间劳动者仍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那将使劳动者陷入“寻求司法救济则其竞业限制期限被延长”“不寻求司法救济则其权益受损害”的两难境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者的司法救济权利。而用人单位无需与劳动者协商,即可通过提起仲裁和诉讼的方式单方地、变相地延长劳动者的竞业限制期限,在一定程度上免除其法定责任,该情形属于《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免除其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应属无效。由此,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本报记者 赵新政